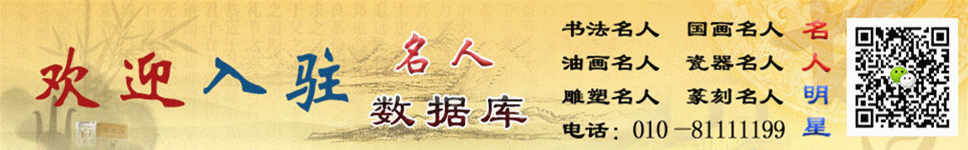
热门点击

栏目推荐

西部歌王—王向荣
时间:2017-08-23
所属栏目:人物访谈

二十五年前,陕北榆林的民间艺术汇演舞台上,王向荣一曲陕北民歌《黄河船夫曲》,随着他扎着白羊肚手巾的形象,风靡大江南北;二十五年后的2008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,年逾花甲的王向荣又吼出了《黄河春雷》的旋律。
还是那个王向荣,穿着陕北高原的红褂子,唱着黄土地的歌,一样的率性纯粹、一样的高亢激情。
不像那个王向荣,伴奏的不是唢呐而是交响乐队,对唱的不是陕北妹子而是城里的合唱团,可黄土高坡田间地头的味儿,依然没有变。
二十五年里,他从榆林的草台班子唱到了人民大会堂;由一个民办教师变为了“西部歌王”。他曾推出民歌专辑,他曾放歌欧洲多国。现在,他还是榆林民间艺术团演员,是十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。他怎么看这25年陕北民歌的变迁,怎么看它的未来?
我是个陕北民歌传承者
问:人们喜欢叫你“民歌大王”,你自己怎么看?
王:我从来不承认我是什么“王”。如果我是“民歌大王”,那陕北的“王”就太多了,我们的上几代人都可以称为“王”。好嗓子的大有人在,我只不过是赶上了这个时代,在国内外流行音乐的冲击下,在陕北民歌几乎将被湮没的情况下,我在那儿坚持唱自己的歌、走自己的路。在这样的情境下,就显得我比较独特,就好像是一个领军人物。
我只清楚一点,我唱歌的时候,是在唱我自己的东西。我把祖先最根本的东西一点一滴地积累到我的身上,然后消化成自己的东西,再以我的方法去呈现。
问:你怎么定位自己的身份?
王:我完全就是一个民歌传承者,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歌传承人。国家也给我颁了一个证,说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—陕北民歌的杰出传承人。就是说在民歌这一块,我是传承人之一,我认为这个还是比较恰当的。老一辈艺人已经不在了,年轻人对陕北民歌艺术又了解甚少,所以对于我来讲,我要做的是把老先人的东西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,再踏踏实实地传承下去。
父老乡亲传给我民歌精神
问:一路走来,影响你歌唱之路的有那些人?
王:陕北黄土地的父老乡亲。我从小跟着父亲上山放羊,他们哼的小曲、小调和信天游非常纯粹,对我的影响很大。家乡一位二人台老艺人给我的印象也很深刻,他90多岁了还想着出去唱歌。那时我已经在省里获奖了,去拜访他的时候,他对我说:“啥时候师父也跟着你去唱歌,我现在的精力还很旺盛。”这些唱民歌的老艺术家们,不管有多少物质上的东西,都代替不了民歌给他的精神头。只要有民歌,他就立起来了;没有民歌,他就塌下去了。我感觉这些人的精神就是民歌的精神。或许很多民歌会逐渐消失,但民歌精神不会消失,因为它是人最本真的东西,是人性的真实表达。
问:取得现在的成绩是靠天赋,还是后天努力?
王:我的天赋就是陕北那块土地。云南的山里养育出来的是“哩哩”音,江南水乡产生的就是丝竹,而陕北的黄土地造就了我的天赋。我觉得后天努力就是你得真正爱它,现在很多搞艺术的人很急功近利,没有从心里真正去爱它。我是真正爱陕北民歌的,我把民歌当作我的事业去追求,而很多人只把唱歌当成工作,这样是唱不好歌的。
民歌的权威评委是老百姓
问:央视青年歌手大赛不断推出原生态唱法和原生态歌手,你对此如何看?
王:青歌赛对民歌的发展还是起到了一些推动作用,但有些方面不尽如人意。给人感觉那几位评委就是权威,我认为对于民歌来说,权威应该是老百姓,最高评委就是民歌所在地的老百姓,对陕北民歌最有发言权的就是陕北人民。电视台给你授予了金奖,但陕北人不承认你,陕北人认为你没味道,那你也是失败的。
还有一点,我认为原生态民歌互相之间是不具可比性的。蒙古长调就是蒙古长调,它怎么能和陕北民歌进行比较呢?陕北民歌是反映黄土高原上人们的思想情感的,内蒙古民歌是马背民族的音乐形式,川江号子则是生活在水上的川渝人民创造的音乐。把它们一锅炒,要评个金奖、银奖,这个做法是不对的。如果定要分个高下,那就云南民歌和云南民歌比,贵州侗族大歌就跟侗族大歌比,这样选出来的才是真正的金奖。民歌和通俗歌曲不一样,通俗歌曲的发音和演唱技巧,不管在哪里都一样,所以通俗歌曲可以统一标准、统一评判,但各地的民歌怎么去统一要求呢?所以青歌大赛评委的看法,我基本不赞同。
“学院派”应该多亲近土地
问:你觉得你这种土生土长的民歌艺人,和艺术学院里培养出来的民歌演唱者有什么区别?
王:这根本就不是一回事。我觉得真正来自民间的艺人们发自内心地演唱出来的东西,这才叫民歌。民歌不能离开那块土地。
民歌也不讲究那么多的演唱技巧,它就是演唱者真情实感的流露,高兴的时候他是喊出来的;痛苦的时候他是哭出来的;忧愁的时候他是哼出来的。他喊出来的、哭出来的和哼出来的东西和学院里的老师讲这个音怎么发、怎么圆润、怎么明亮,不是一回事。
我认为学院里的民歌手应该到民间去,去亲身体验民间真正的东西,这才是民歌艺术的真谛。我不反对把歌唱得更好,但演唱的方法是为歌曲的情感服务的,一个是实质、一个是形式,本末不能颠倒。
为适应观众民歌可以“变”
问:如今演绎民歌,你更倾向于哪种演绎方式?是那种原汁原味的演唱方法还是像这次这种交响乐伴奏的形式?
王:我觉得都可以。为了让更多的人接受民歌、了解民歌,像“上海之春”推出的这种交响信天游的方法是可取的。信天游也是有节奏的,只要和乐队磨合好,就能融合在一起。
问:这样下来,民歌的某些元素会不会就减少了呢?
王:不会减少,我和很多乐队合作过。民歌手要摆正自己的位置,坚持按照自己的唱法演唱,乐队只是起烘托作用。
问:你觉得民歌发展的这两条路,哪一条对民歌的前途更有利?
王:老百姓当然喜欢田间地头的歌,那是民歌赖以生存的环境。歌手只要自己的功夫扎实,在田间地头还是在音乐厅里,就无所谓了。为了适应观众的变化,民歌在形式上肯定需要一些改变。在老民歌的基础上注入新的内容,这是有利于传承的,这要看你从哪个层面理解它。
问:听说你喜欢黑人音乐?
王:是的,黑人的歌是发自内心唱出来的,也是一代代传承下来的。演唱者也是随着自己的性子在唱,他想在哪儿停就在哪儿停,想唱多长就多长。我听他们的唱片,总会产生一种幻象:黑人在哪儿啊,陕北在哪儿啊。我总感觉黑人唱的不就是陕北的风俗音乐么,这就是音乐的奇妙之处吧。
唱信天游的年轻人多了
问:现在陕北唱信天游的年轻人多吗?
王:通过全社会的努力,现在喜欢陕北民歌的年轻人比前几年多了。对于民歌的前途,前几年我是很担心的,现代音乐的冲击太大了,前几年在媒体上几乎找不到民歌的影子。这几年大家的态度有所改变,政府也开始重视,这让我们这些民歌艺人看到了希望,现在我比以前乐观多了。
问:你对民歌的传承和发展怎么看?
王:现在唱陕北民歌的年轻人,对民歌的了解还不够,积淀还不深。他们只是听录音带,跟着学唱民歌,太急功近利,还没了解民歌的精髓,这对民歌的发展也是绝对不利的。年轻人的历练不够,对民歌的认识不够,还是让我很担忧。现在我在陕西的10多所大学当客座教授,连说带唱一教就是几个小时。虽说只有很少的报酬,但是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为民歌做些事情。
问:你认为新人的培养应该走哪条路子?是从学院里面培养新人还是从民间寻找好苗子?
王:我认为都是可以的,学校里确实喜欢民歌的青年人,也是可以成为优秀的民歌手的。真正爱民歌的人,是会主动去生长民歌的土壤里汲取营养的。
问:现在的新人还有像你这样从民间生长起来的可能性吗?
王:我觉得有可能,但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经历的环境是不一样的,陕北本身也变了。
问:现在陕北的田间地头还能听到信天游吗?
王:生存环境变了呀,很多人都出去打工了,生活方式也变了,已经很少能听到了。我希望大家能多关心民歌一些。黑人音乐在国际上的发展已经让我看到了希望,民歌也会有那一天的。
上一篇:许谨伦


